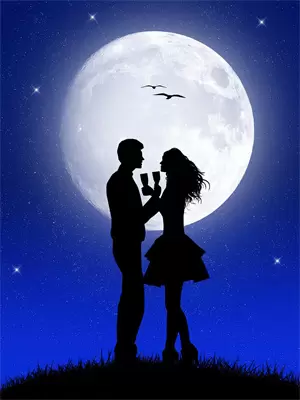经历两次废黜,半生圈禁,太子胤礽重生后,人生目标:混吃等死,安稳到老。
面对康熙的考校,他张口“皇阿玛圣明”,闭口“儿臣愚钝”。直到边疆急报,他跪地请辞,
康熙拍案而起:“想跑?没门!给朕老老实实当皇帝!”乾清宫东暖阁里,
太子胤礽垂手侍立在御案旁,眼观鼻,鼻观心,姿态恭谨得无可挑剔。他微微低着头,
视线落在自己杏黄色蟒袍的前襟缝线上,不敢,也不愿去触碰那道来自御案后的目光。
那目光,属于他的皇父,康熙皇帝。御案后,康熙正批阅着奏章,朱笔偶尔划过纸面,
发出细碎的沙沙声。殿内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,咚,咚,一下下,敲在胤礽的耳膜上。
这寂静,比前世那些囚禁岁月里的死寂,更让他心惊肉跳。他是胤礽,大清朝的皇太子,
也是……一个从康熙五十一年那场废黜与圈禁的噩梦中,挣扎着爬回来的孤魂野鬼。
那场持续了十余年的幽禁,耗尽了他所有的骄傲、野心和生气。冷饭残羹,高墙孤影,
兄弟们的踩踏,皇父最终的厌弃……一切的一切,如同冰冷的烙印,深深刻在他的魂魄里。
再睁开眼,竟是康熙三十六年!他还是那个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储君,风华正茂,
圣眷正浓。可这“正浓”的圣眷,如今在他眼里,不过是裹着蜜糖的砒霜。前世,
他就是太过相信这份独一无二的恩宠,太过锋芒毕露,才落得那般下场。结党营私?
骄纵妄为?不,最根本的,是他这个太子做得“太好”了,好到让皇父感受到了威胁。
这一世,他什么都不要了。什么贤名,什么政绩,什么属于储君的威仪……他只要活着,
安安稳稳地活着。“保命”,成了他重生归来唯一的目标。如何保命?藏拙,示弱,
让皇父觉得他无能,觉得他离不开皇父的教导,觉得他这个太子,完全在皇父的掌控之中。
“胤礽。”康熙的声音不高,带着惯有的威严,打断了他的思绪。胤礽心头一凛,
立刻上前半步,躬身:“儿臣在。”康熙将一份奏折往他这边推了推,
语气平淡无波:“河南巡抚递上来的,说了些黄河堤防修缮的条陈。你也看看,
说说你的想法。”来了。胤礽双手接过那本沉甸甸的奏折,指尖几不可查地蜷缩了一下。
他展开,目光快速扫过。康熙三十六年夏,河南境内黄河几处险工确有此议,
前世他还曾就此与工部官员详细论证,提出过数条切中肯綮的见解,引得皇父当时连连点头,
目露赞赏。可现在……他在心里无声地吸了口气,
强迫自己压下那些几乎要脱口而出的专业论断。他看得懂这奏折里提议的疏漏在哪里,
用料估算的不足,民夫调派的不妥……每一点,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但他不能说。
他酝酿了一下情绪,抬起脸时,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茫然与羞愧,将奏折轻轻合上,
双手奉还,声音也低了几分:“回皇阿玛,这……这奏折所言,工程浩大,条陈繁复,
儿臣……儿臣愚钝,一时看得不甚明白,其中关窍,难以把握。恐……恐妄加评议,
有失妥当。还请皇阿玛圣裁独断,或……或教导儿臣。”他垂下眼睑,等待着预料中的失望,
或者,是皇父那深不见底的审视。然而,他等来的,却是一段长得令人心慌的沉默。
东暖阁里,只有那龙涎香,还在不知疲倦地袅袅盘旋。康熙没有立刻说话。
他看着眼前这个低眉顺目、口称“愚钝”的儿子,眉心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。就在刚才,
胤礽恭敬地说出“儿臣愚钝”的那一刻,一个截然不同的、清晰而沉稳的声音,
毫无预兆地撞进了他的脑海——……这陶庄引河一处,土质松软,仅以碎石夯土,
如何抵挡伏秋大汛?至少需打入丈二木桩,以‘梅花桩’法固基。还有这料银估算,
分明是照着往年太平水情的旧例,若遇险情,必捉襟见肘,至少需再增三成备银,方能无虞。
民夫征调更是可笑,岂有不顾农时之理?当分批次,以工代赈,方是上策……这声音?
康熙握着朱笔的手指,倏地收紧了。他猛地抬眼,目光如电,直直射向胤礽。
胤礽依旧保持着躬身的姿势,脸上那恰到好处的惶恐和无措,没有半分破绽。
可那脑海里的声音,言之有物,一针见血,
每一条都精准地点在了这份奏折提议最致命的弱点上!这哪里是“愚钝”?
这分明是洞若观火,是老成谋国!这是……胤礽的心声?
康熙被自己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惊住了。他自幼登基,擒鳌拜,平三藩,收台湾,
历经无数风浪,自问这世上已少有能让他失态之事。可眼下这情形,
实在超出了他理解的范畴。他能……听见太子的心里话?为了确认,康熙不动声色,
将语气放得更缓,带着试探:“哦?一点想法也无?朕记得,你往日对河工之事,
也并非全然不通。”胤礽心里咯噔一下。往日?往日他就是太“通”了!他头垂得更低,
声音里甚至带上了一丝惶恐的颤音:“皇阿玛明鉴,儿臣……儿臣往日不过是拾人牙慧,
纸上谈兵。如今细看这般实务,才知其中艰难深奥,非儿臣所能妄测。
儿臣……恳请皇阿玛教诲。”往日是往日,现在是现在。再说多错多,做多错多。
这太子之位,就是个烧红的烙铁,谁爱碰谁碰去,我只求安安稳稳混个亲王,
老死床榻就谢天谢地了。皇阿玛,您就别试探儿子了,儿子真的什么都不想要,
只想活命……又一串心声,带着明显的惫懒和……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怼与恐惧,
清晰地传入康熙脑中。康熙沉默了。他看着胤礽那副恨不得把自己缩进地缝里的样子,
再听着脑海里那一番与表面姿态截然不同、甚至可称“大逆不道”的心里话,一时间,
心绪翻涌,复杂难言。这混账东西!他竟存了这样的心思?只想混个亲王老死?这大清江山,
这储君之位,在他眼里竟成了洪水猛兽,烧红的烙铁?一股无名火猛地窜上康熙心头,
几乎要冲破他多年的帝王修养。他是对太子近年的一些行为有所不满,是曾动过敲打的心思,
可从未想过,太子内心深处,竟是这般……这般毫无担当,贪生怕死!然而,那怒火之下,
另一股更深沉、更细微的情绪,也在悄然滋生。是因为朕吗?是因为朕平日的严苛?猜疑?
还是因为……上次废太子时,自己那不容置喙的决绝,终究在他心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阴影?
康熙的思绪,不由得飘向了那遥远而痛楚的记忆尽头,那是他心底最不愿触碰的角落之一。
他看着胤礽低垂的、显得异常柔顺脆弱的脖颈,听着他心里那带着惊惧的“只想活命”,
那句已经到了嘴边的斥责,终究是咽了回去。殿内再次陷入沉寂。良久,
康熙才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,那叹息轻得像一阵风,吹散了空气中些许凝滞的尘埃。
他重新拿起朱笔,在那份奏折上批阅起来,声音恢复了平静,
甚至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疲乏:“罢了。你既无想法,便先退下吧。河南之事,
朕自有主张。”“是,儿臣告退。”胤礽如蒙大赦,恭敬地行礼,一步步倒退着出了东暖阁。
直到转身踏出殿门,初夏略显炙热的阳光扑面而来,他才感觉自己那颗悬在冰窟里的心,
稍稍回落了一点。后背的里衣,不知何时,已被冷汗浸湿,紧贴着皮肤,
带来一阵黏腻的凉意。他刚才……应该演得还算成功吧?皇父那片刻的沉默,是什么意思?
失望?还是……怀疑?胤礽不敢深想,只是加快了脚步,只想尽快离开这令人窒息的乾清宫。
东暖阁内,康熙却并未继续批阅奏章。他搁下朱笔,身体向后,靠在明黄色的团龙靠垫上,
阖上了双眼。指尖,无意识地摩挲着温凉的玉扳指。胤礽……那些心声,
那些与他表面恭顺截然相反的、精辟甚至堪称老辣的分析,
还有那深藏其间的恐惧与惫懒……一遍遍在他脑海中回响。这小子,到底是怎么回事?
他这看似完美的藏拙之下,究竟隐藏着什么?是真的心灰意冷,毫无大志?
还是……一种以退为进,连他自己都未曾全然察觉的、更深沉的机心?康熙睁开眼,
目光深不见底,望向殿外胤礽离去的方向。良久,他低沉的声音在空寂的暖阁内响起,
带着一丝无人能解的复杂意味:“胤礽……朕,倒要好好看看你了。”胤礽走出乾清宫,
初夏的阳光明晃晃地照在他杏黄色的太子袍服上,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。
后背那一片被冷汗浸湿的凉意,此刻在阳光下非但没有驱散,反而激起一阵更深沉的寒意。
皇阿玛最后的沉默,像一块巨石压在他心头。不对劲。前世,
他若是在河工之事上表现得如此“愚钝”,皇阿玛即便不当面斥责,
眼神里也必然会流露出失望与不悦。可刚才,皇阿玛的眼神……太复杂了。
那不是单纯的失望,更像是一种探究,一种仿佛要穿透他这副恭顺皮囊,
直抵灵魂深处的审视。难道……自己藏得还不够深?还是哪里露出了马脚?
胤礽心头警铃大作。他重生归来,最大的依仗便是对未来的“预知”和对皇阿玛脾性的了解。
可若皇阿玛的反应超出了他的预料,那变数就太大了。他必须更小心,更谨慎。藏拙,
不仅仅是表现得无能,更要表现得……需要皇阿玛。接下来的日子,
胤礽将“需要皇阿玛”这五个字贯彻到了极致。每日的晨昏定省,他从不缺席,
且每次都掐着点儿,在康熙处理政务间隙,或是用膳前后出现。
请安的话也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,但姿态做得十足。“儿臣给皇阿玛请安,
皇阿玛昨日歇得可好?今日天气转热,还请皇阿玛保重龙体。”他捧着一个小食盒,
里面是御膳房新制的、据说是江南风味的清爽糕点,“这是儿臣尝着觉得尚可的,
想着皇阿玛或许能用一些。”前世这时,皇阿玛似乎有些苦夏,胃口不佳。这糕点清爽,
应该合口味。送不送在我,吃不吃在他,总归是个心意。不求他多看重,只求他记得,
我这个儿子,心里是念着他的。康熙看着那食盒,
又看看胤礽那低眉顺眼、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盼胤礽努力装出来的的样子,
再听着脑海里那番“不求看重,只求念着”的心声,心情又是一阵复杂。他捻起一块糕点,
尝了尝,味道确实清爽。“有心了。”“皇阿玛喜欢就好。
”胤礽脸上适时地露出一丝“被肯定”的欣喜,随即又转为“谦逊”,“儿臣愚笨,
不能为皇阿玛分忧国事,只能在这些小事上尽尽心了。”分忧?可不敢分忧。分着分着,
就该忧心我这个太子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。还是这样好,送送点心,问问冷暖,安全。
康熙拿着糕点的手顿了顿,若无其事地放下。“嗯,下去吧。”“儿臣告退。”人走了,
那心声却还在康熙耳边回荡。“安全”……这两个字,像针一样,轻轻扎了他一下。议政时,
康熙故意将一些并不算核心、但也能看出能力的事务交给胤礽。“胤礽,
宗人府报上来几个闲散宗室子弟的安置,你拿个章程看看。
”胤礽心中立刻浮现出前世处理类似事务时,几个既顾全宗室体面,
又不至让朝廷负担过重的成熟方案。但他面上却露出恰到好处的为难。“皇阿玛,
这……宗室事务,关系天家颜面,儿臣年轻,只怕考虑不周,处置不当,反伤了和气。
可否……可否请皇阿玛先给儿臣划定个大概的方略,儿臣遵照办理,若有不明,
再来请皇阿玛示下?”按例给银、给田,不纵不苛便是上策。具体数目,按亲疏、按品级,
都有旧例可循,稍作调整即可。但这话我不能说,说了就显得我太熟悉这些‘俗务’,
显得有手腕。还是让皇阿玛定个调子,我跑跑腿最稳妥。康熙听着他心里的“上策”,
再看看他嘴上“年轻”、“考虑不周”的推脱,只觉得一股气闷在胸口。这小子,
肚子里明明有货,偏要装出一副草包样子!他忍着把那“上策”直接点破的冲动,
沉声道:“既如此,朕让宗人府循旧例,你盯着些,莫出纰漏。”“儿臣遵旨,
定当尽心竭力,不负皇阿玛信任。”胤礽恭敬领命,心里却松了口气。过关。
既接了差事显得听话,又没自作主张,一切按旧例,出了错也怪不到我头上。完美。
康熙:“……”他捏了捏眉心,挥挥手让胤礽退下。再听下去,
他怕自己会忍不住把这装模作样的小子揪过来揍一顿。对待兄弟们,
胤礽也一改前世或倨傲、或防备、或刻意拉拢的态度。遇到直郡王胤禔,他主动停下脚步,
客气地打招呼:“大哥这是刚从兵部出来?辛苦了。” 甚至还会貌似不经意地提一句,
“听闻大哥前些日子偶感风寒,可大安了?” 老大虽然心思重,爱揽权,
但面上功夫得做。他这人吃软不吃硬,给个台阶,他至少明面上不会太难堪。
胤禔显然没料到太子会主动关心他,愣了一下,才板着脸回道:“劳太子挂心,已无碍。
” 心里却嘀咕,这太子,最近怎么像是转了性?遇到胤祉,他会聊聊书画,说说古籍,
但绝不深入,只停留在风雅趣闻层面。“三弟近日又得了什么好帖?若有拓本,
可否让二哥也观摩一二?” 老三心思细,爱钻营,但学问是好的。与他谈学问,最安全,
也显得我这个太子重视文教。胤祉自然是笑着应承,觉得太子比以往亲和了许多。
遇到胤禩、胤禟、胤䄉这些年少的弟弟,他更是摆出温和兄长的姿态。胤禩敏感细致,
他便偶尔过问一下其生母良妃的病情凭借前世记忆,他知道此时良妃身体已有些不适,
叮嘱太医好生照看。胤禟、胤䄉活泼好动,他便将一些内务府进上来的新奇玩意儿,
挑些不打眼的赏给他们。老八将来是个厉害角色,现在施些小恩,结个善缘,
总比将来成为死敌好。老九老十,现在还是半大孩子,给点小玩意就能高兴半天,成本低,
见效快。康熙冷眼旁观着胤礽的这些“小动作”,听着他那些算计得清清楚楚的“心声”,
心情越发难以言喻。这小子,把“兄友弟恭”也当成了一门需要精确计算的功课!每一步,
每一句话,都带着明确的目的——不结怨,不树敌,广结善缘,以求自保。他做得如此自然,
如此……滴水不漏。若非自己能听见他的心声,
恐怕也会被他这副温和谦逊、关爱兄弟的表象所迷惑,以为他经历了一番挫折,终于长大了,
懂事了。可这“懂事”的背后,却是如此的算计和深深的恐惧。康熙坐在乾清宫的龙椅上,
望着殿外湛蓝的天空,第一次对自己一贯笃信的“帝王心术”和“驭下之道”,
产生了一丝不确定的动摇。他把太子,把他的儿子,逼到了何种境地?
才会让他宁愿自污藏拙,将一身才华尽数掩埋,只为了……活命?而自己,
这个能听到他心声的父亲和皇帝,又该如何对待这个心思深沉却又可怜可叹的儿子?
是继续看着他表演,顺水推舟,让他“如愿”做个平庸太子,安稳余生?
还是……康熙的目光,缓缓落在那堆积如山的奏折上,眼神渐深。就在这时,
兵部一份六百里加急的文书,被太监急匆匆地送了进来。“皇上,西北噶尔丹部又有异动,
骚扰边境,甘肃提督急报!”康熙展开军报,快速浏览,眉头紧紧锁了起来。
噶尔丹虽经上次亲征重创,但残余势力仍在草原上流窜,不时寇边,如同附骨之疽,
难以根除。此次规模似乎不小,边关守将压力巨大。他沉吟片刻,
心中已有了几个人选派兵增援的方案,但总觉得不够完美,难以彻底解决问题。忽然,
他心念一动,想到了一个人。“传太子。”康熙的声音在寂静的殿中响起,
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味。他倒要看看,面对这等真正的军国大事,
他这个“愚钝”、“需要皇父教导”的太子,心里又在想些什么?那被刻意掩藏的锋芒,
是否还能继续藏得住?胤礽再次踏入乾清宫时,敏锐地察觉到气氛与往日不同。
空气中弥漫着硝烟未至的紧绷,皇阿玛眉宇间是挥之不去的沉郁,御案上摊开的,
正是那份边关急报。“儿臣叩见皇阿玛。”他依礼参拜,心头警醒。军国大事,历来敏感,
他打定主意,今日更要谨言慎行,绝不多说一个字。“起来吧。”康熙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,
他将那份军报往胤礽面前推了推,“甘肃提督急奏,噶尔丹残部再度集结,侵扰边境,
劫掠牛羊,杀害边民,气焰嚣张。你看看。”胤礽心头一跳。噶尔丹!
这个前世纠缠了皇阿玛大半生的名字,他再熟悉不过。康熙三十六年这次侵扰,
规模不算最大,但位置刁钻,行动迅捷,前世边军应对失当,颇有些损失,
后来还是费扬古领兵出击,才将其暂时击退。他双手接过军报,目光快速扫过。果然,
与记忆中的情报分毫不差。
敌军主力藏匿于……进军路线应是……若以一部精兵绕行至……断其归路,
再以……一个个清晰无比的战术方案,几乎是本能地在他脑海中飞速成型、推演。
他太了解此时的噶尔丹部,了解他们的作战习惯,了解那片草原的地形,
更了解前世此战得失。但他立刻强行掐断了这些思绪。不能想!绝不能让皇阿玛察觉半分!
他努力放空大脑,专注于军报上的文字,脸上适时地露出凝重、愤慨,
以及……恰到好处的茫然无措。“噶尔丹贼心不死,实在可恨!”他放下军报,
语气带着符合身份的愤怒,随即转为“忧心”与“无助”,“边关百姓受苦了……只是,
这用兵之道,深奥艰险,儿臣……儿臣于此道实在粗浅,不敢妄言。皇阿玛运筹帷幄,
定有良策破敌,儿臣……一切听凭皇阿玛圣裁。”派费扬古!让他率麾下精锐,轻装疾进,
直扑敌军辎重所在!噶尔丹残部补给困难,断其粮草,其军自乱!
另可命甘肃总兵孙克思部正面佯动,吸引注意……不行,不能想!皇阿玛,您快说吧,
派谁去都行,只要别问我意见就好。我只想平平安安在京城待着。康熙端着茶盏的手,
停在半空。他听着胤礽嘴里那套“粗浅”、“不敢妄言”的说辞,
再听着脑海里那套目标明确、步骤清晰、直指要害的破敌方略,只觉得一股气血直冲顶门。
好一个“粗浅”!好一个“不敢妄言”!这小子心里明明装着足以扭转战局的良策,
却在这里跟他演什么忠厚无知!
扬古”、“断其粮草”、“正面佯动”……每一条都精准地打在了噶尔丹此番行动的七寸上!
比他刚才在心中权衡的几个方案,都要犀利,都要有效!康熙胸口剧烈起伏了一下,
他强行压下几乎要脱口而出的质问,将茶盏重重顿在案上,发出“砰”的一声闷响。
胤礽吓得一哆嗦,头垂得更低,心中骇然:怎么了?我说错什么了?
难道表现得还不够无能?康熙看着他这副鹌鹑样子,气更是不打一处来。他死死盯着胤礽,
眼神锐利如刀,仿佛要将他从里到外剖开。殿内死寂。落针可闻。良久,
康熙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,声音冷得能掉出冰碴子:“朕知道了。你,退下。”“是,是,
儿臣告退。”胤礽如蒙大赦,几乎是手脚并用地退了出去,后背瞬间又被冷汗浸湿。
皇阿玛刚才那眼神,太可怕了,仿佛……仿佛能看穿他的五脏六腑。翌日,乾清宫朝会。
关于西北用兵的方略,几位重臣意见不一,有主张固守的,有主张派大将迎头痛击的,
争论不休。康熙高踞龙椅,面无表情地听着。直到众人声音渐歇,他才缓缓开口,声音不高,
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:“噶尔丹残部,疥癣之疾,然其劫掠边民,动摇国本,不可不除。
然则,与其劳师动众,大军围剿,不如以精骑击其要害。”他目光扫过殿内文武,
最终落在兵部尚书身上。“着,振武将军费扬古,即刻率所部精锐骑兵八千,轻装简从,
绕行巴丹吉林沙漠南缘,直插敌军位于额济纳河的辎重囤积之地,务必将其焚毁殆尽!
”“着,甘肃总兵孙克思,率本部兵马,于正面摆出决战态势,大张旗鼓,
吸引噶尔丹主力注意,为费扬古部创造时机。”“两军需密切联络,以快打慢,
务求一击奏功,扬我大清国威!”旨意清晰,战术明确,甚至具体到了行军路线和作战目标!
殿内众臣先是一静,随即纷纷露出恍然与钦佩之色。“皇上圣明!”“此计大妙!直捣黄龙!
”“断其粮草,噶尔丹必不战自溃!”唯有站在百官之前的胤礽,如遭雷击,僵立在原地,
脸色瞬间煞白。这……这分明是他昨日在心里盘算,却死死摁住不敢吐露半个字的方略!
连细节都分毫不差!怎么会……皇阿玛怎么会……一股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,
血液都仿佛冻僵了。他感觉龙椅上那道目光,似乎不经意地扫过他,
带着一种深不见底的意味。接下来的日子,对胤礽而言,如同置身于油锅之上,备受煎熬。
边关战报不断传回,一切正如“预料”般发展。费扬古部成功奇袭额济纳河,
焚毁噶尔丹大量粮草辎重,孙克思部正面牵制得力。噶尔丹部猝不及防,军心大乱,
仓皇北窜,大清边患暂解。捷报传回京师,朝野欢庆。
康熙在朝会上褒奖了费扬古、孙克思等将士,神色却平静无波,
仿佛这一切早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只有胤礽知道,这“掌握”从何而来。他躲在毓庆宫中,
坐立难安。皇阿玛能看穿他的心思!这个认知如同鬼魅,缠绕着他,让他寝食难安。
他试图控制自己的思绪,可越是压抑,
那些关于朝局、关于人事、关于未来的种种判断和“先知”,就越是纷乱地涌现。
在康熙面前,他感觉自己就像个被剥光了衣服、毫无秘密可言的透明人!
这比他预想中最坏的情况,还要糟糕百倍!藏拙?在一個能看穿你所有伪装的人面前,
藏拙有何意义?示弱?在一個清楚知道你底牌的人面前,示弱更像是一种讽刺和挑衅!
他之前的种种表演,在皇阿玛眼里,恐怕如同跳梁小丑!恐惧,如同冰冷的藤蔓,
紧紧攫住了他的心脏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!必须改变策略!既然藏不住,那……就彻底放手!
数日后,康熙正在批阅关于战后赏功的奏章,梁九功躬身进来禀报:“皇上,
太子殿下在外求见,说……有要事陈奏。”康熙笔尖一顿,抬起眼。“传。”胤礽走了进来,
步伐沉稳,但脸色是一种近乎决绝的苍白。他撩起袍角,端端正正地跪倒在御案前,
以头触地。这个举动,让康熙微微蹙眉。非年非节,非重大场合,行此大礼……“儿臣胤礽,
叩请皇阿玛圣安。”“起来说话。”康熙放下朱笔,目光落在他身上。胤礽却没有起身,
反而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奏疏,高高举过头顶。“皇阿玛,儿臣近日,夜不能寐,反复思量,
深觉才疏学浅,德不配位,实在不堪储君重任,有负皇阿玛多年教诲与期望。
”他的声音带着刻意维持的平静,却掩不住那细微的颤抖,“儿臣……恳请皇阿玛,
废黜儿臣太子之位!允儿臣……做一个闲散宗室,为大清,为皇阿玛,祈福终老!
”他将奏疏再次往高举了举,额头紧紧抵着冰冷的地砖,闭上了眼睛。既然您什么都知道,
知道我所有的伪装,知道我所有的恐惧,也知道我……或许有那么一点能力。那这太子之位,
于我便是催命符,于您便是心头刺。我不要了!我什么都不要了!只求您看在父子情分上,
放我一条生路!让我远离这旋涡中心,苟全性命于世间!我斗不过您,我认输!我只想活着!
轰——!康熙脑中仿佛有什么东西炸开了。他听着胤礽那字字泣血般的“恳请”,
再听着他心里那几乎崩溃的、带着绝望的呐喊,看着他以头杵地、卑微乞命的姿态,
连日来积压的复杂情绪——那被欺瞒的恼怒,那发现才华的惊异,那知其恐惧的怜悯,
那恨铁不成钢的愤懑——在这一刻,尽数化为滔天怒意!“认输”?“苟全性命”?
他爱新觉罗·玄烨的儿子,大清朝的皇太子,竟然如此没有担当!如此贪生怕死!
竟然要将这万里江山,将这祖宗基业,如同敝履般抛弃!“放肆!”康熙猛地一拍御案,
霍然起身!沉重的紫檀木御案被拍得剧烈一震,笔墨纸砚齐齐跳起。他指着跪伏在地的胤礽,
脸色铁青,胸脯剧烈起伏,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带着雷霆般的威压,
响彻整个乾清宫:“朕不准!”“爱新觉罗·胤礽!你这江山,不要也得要!
”康熙那一声“朕不准!”如同惊雷,炸得胤礽魂飞魄散。他伏在地上,浑身僵硬,
连血液都仿佛凝固了。“你这江山,不要也得要!”这句话,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铁锤,
狠狠砸在他的心口。前世被废时的诏书,
那些“不法祖德、不遵朕训、暴虐淫乱、肆恶虐众”的罪名,如同鬼影般在他眼前晃动。
他以为自己主动放弃,能换来一线生机,却没想到,换来的是更决绝的禁锢。
皇阿玛……连他放弃的权力,都要剥夺吗?巨大的恐惧和绝望,几乎将他吞噬。
康熙胸膛剧烈起伏,看着下方那个抖得如同风中落叶的儿子,怒火中烧的同时,心底最深处,
却也掠过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刺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