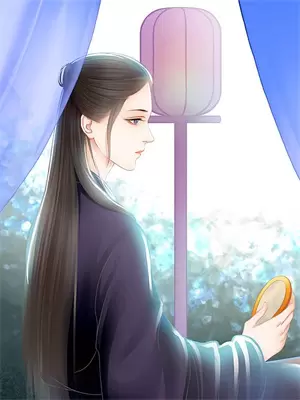楼梯是老的,水泥抹的,边角都磨圆了。灯是声控的,可它懒,你得用力跺脚,
它才不情不愿地亮一下,昏黄的光,像死鱼的眼。我数着台阶,一层,两层,
三层……按理说,该到底了。可拐个弯,还是楼梯,向上,向下,都淹没在更深的黑暗里。
空气里有股味儿,像是尘土,又像是……霉烂了很久的纸。脚步声不对。除了我自己的,
还有另一个。很轻,跟在我后面,不紧不慢。我停,它也停。我走,它又响起。我猛地回头,
用手电筒照过去——空的,只有我自己的影子,被拉得又长又扭曲,贴在冰冷的墙上。
我开始跑。我不再数台阶了,我只想找到那扇该死的、通往大厅的门。汗水流进眼睛,
涩得发痛。我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,在狭窄的通道里撞来撞去。然后,我听见了笑声。
不是男人的,也不是女人的。那声音很细,像一根冰冷的针,从耳朵眼里扎进来。“新来的?
”那声音说。我僵住了,手电筒的光柱在颤抖的墙壁上乱晃。“迷路了?”声音又响起来,
这次,好像就在我脖子后面。我甚至能感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凉气。我不敢回头。老人们说,
走夜路,听到有人叫你,千万别回头,肩膀上的阳火会灭。我咬着牙,继续往下跑。
脚下一滑,差点摔倒。我低头,用手电一照——台阶上,散落着几张纸钱。黄裱纸,
中间方方的孔,边缘烧过的痕迹是黑色的。刚才还没有。冷汗湿透了保安服的衬里。
不知又跑了多久,我看到了那扇门。熟悉的,刷着绿漆的铁门。门把手就在那儿。
我的心几乎要跳出嗓子眼。我冲过去,拧动把手——锁死的。不对,我进来时,
它明明是开着的!我用尽全身力气去撞,门纹丝不动,只发出沉闷的响声,
像敲在一口棺材上。绝望像冰水,从头顶浇下来。我靠着门滑坐在地上,手电筒也滚到一边,
光斜斜地照着对面的墙壁。那面墙……刚才跑过时没注意,那面墙上,布满了划痕。
不是随便的刻划,是一个个数字,密密麻麻,写满了整面墙。“十三,十三,
十三……”全是“十三”。我们这栋楼,根本没有十三层。十二层上面,就是十四层。
这是规矩,避讳。可这里,满墙都是。我看着那些数字,它们好像活了过来,
像蚂蚁一样在墙上爬。那个细针一样的声音,又在我脑子里响起来,这一次,它不是在问,
而是在数。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它数得很慢,很清晰。
“……十一、十二……”我捂住了耳朵,没用。那声音是从我骨头缝里钻出来的。
它停了一下。然后,轻轻吐出两个字。“十三。”手电筒的光,嗤啦一声,灭了。
彻底的黑暗。粘稠得如同墨汁。我听见自己的心跳,咚,咚,咚,像一面破鼓。
还有另一个声音。滴答。滴答。像是水龙头没关紧。可这楼梯间里,哪来的水龙头?
那水滴的声音越来越近,越来越响。一股铁锈味,混着更浓的霉烂气味,弥漫开来。
有什么东西,在黑暗中,正一步一步,向我靠近。我不能死在这儿。我猛地爬起来,
在黑暗中胡乱摸索。我摸到了冰冷的墙壁,摸到了那些刻着“十三”的划痕。
我的手指被粗糙的水泥边缘划破,但我感觉不到疼。我沿着墙根爬。我不知道方向,
我只想离那滴答声远点。然后,我的手指触到了一个空洞。是一个通风口,百叶窗掉了一半。
很小,但足够我这种瘦子钻进去。我什么也顾不上了,扒着边缘,像一条濒死的狗,
拼命往里挤。里面是通风管道,更窄,更黑,全是灰尘。我只能在里面匍匐前进,
金属管道硌得我骨头生疼。我不知道爬了多久,直到看到前面似乎有一点微光。
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,向那光亮撞去。哐当一声,我连同几片松动的挡板一起摔了出去。
光刺得我睁不开眼。清新的空气涌入肺部,我剧烈地咳嗽起来。我躺在地上,看着头顶。
那是天花板,普通的,办公室的天花板,嵌着明亮的日光灯管。我出来了。我还在大楼里,
但这里是大厅旁边的走廊。安全,正常。天快亮了,窗外透进熹微的晨光。我挣扎着坐起来,
回头看去。我出来的地方,是一个墙角的检修口,平时用一块踢脚板挡着,毫不起眼。
几个早来的同事看见我,一脸惊愕。“林七?你怎么从这儿钻出来了?身上怎么搞的?
”我低头,崭新的保安服又脏又破,沾满了灰尘和……一些暗红色的、已经干涸的斑点。
那不是我的血。队长走过来,皱着眉:“你跑哪儿去了?签到表也没划!
我们正准备换班找你呢!”我张了张嘴,却发不出声音。我能说什么?
说我在楼梯间里遇到了鬼打墙?说有个声音数到了十三?说我在黑暗里爬了通风管道?
没人会信。我只是摇了摇头,哑着嗓子说:“没事,摔了一跤,迷路了。”队长将信将疑,
拍了拍我的肩膀:“新人嘛,第一次夜班,紧张是正常的。去洗把脸,换衣服下班吧。
”我点点头,踉跄着走向洗手间。拧开水龙头,冰冷的水冲在脸上,让我稍微清醒了些。
我抬起头,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脸色苍白得像纸,眼圈乌黑。我扯了扯嘴角,
想给自己一个安慰的笑。镜子里的我,也扯了扯嘴角。可是,它的笑容没有停,
嘴角一直向上咧,咧到了一个正常人绝对达不到的弧度,露出了全部牙龈,
像一个无声的、狰狞的嘲笑。它的眼睛,直勾勾地看着我,没有瞳孔,只有一片浑浊的白。
然后,它抬起手指,沾了沾洗手台上溅的水渍,在镜面上,慢慢地,写了一个字。
那不是一个完整的字,只是一个笔画。一横,一竖……像是一个“十”字的开头。水迹淋漓,
向下流淌。我猛地后退,脊背狠狠撞在冰冷的瓷砖墙上。镜子里的那个“我”,缓缓地,
缓缓地,摇了摇头。我盯着镜中那个扭曲的自己,胃里翻江倒海。那不是幻觉。
嘴角撕裂的弧度,眼中浑浊的白,还有镜面上那未写完的“十”字,水痕像血一样往下淌。
我猛地转身,后背紧贴冰冷的瓷砖墙,大口喘气。“林七?你没事吧?
”外面传来同事的喊声。“没……没事!”我强迫自己镇定,拧开水龙头,
用冷水狠狠冲了把脸。再抬头时,镜子里只有我苍白失措的脸。那个诡异的笑,
那个未写完的字,消失了。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过度惊吓后的错觉。但我知道不是。
衣服上那些暗红色的干涸斑点,像锈迹,又像凝固的血,粘在崭新的保安制服上,刺眼得很。
交班时,队长老张瞥了我一眼,没多问,只是在签到表上替我划了勾。
那支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,让我没来由地想起昨夜楼梯间里,那细如针尖的笑声。
“回去好好睡一觉。”老张把钥匙串递还给我,眼神在我沾着污渍的袖口停留了一瞬,
“新人嘛,第一次夜班,难免的。”我点点头,喉咙发紧,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回到租住的简陋房间,阳光透过脏污的玻璃窗照进来,驱不散骨子里的寒意。
我脱下那身保安服,团起来,想扔,手却僵在半空。最后,
我还是把它塞进了床底最深的角落。可我睡不着。一闭眼,就是无尽的楼梯,昏黄的声控灯,
墙上密密麻麻的“十三”,还有那滴答作响、越来越近的水声,
和脖颈后那丝若有若无的凉气。傍晚,我挣扎着爬起来,头重脚轻。看着窗外渐沉的夕阳,
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紧了心脏。又该去那个地方了。我必须去。这份工作,是我唯一的活路。
走进保安室,晚班的老李正准备下班。他看到我,咧开嘴笑了笑,
露出被烟熏黄的牙:“小子,昨晚吓破胆了吧?听说你从检修口爬出来的?
”我勉强扯了扯嘴角。“别瞎打听,”老张在一旁沉声道,递给老李一支烟,“干活。
”老李接过烟,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,叼着烟晃晃悠悠走了。保安室里只剩下我和老张。
烟雾缭绕,气氛有些沉闷。“老张……”我犹豫着开口,
“那楼梯间……”他猛地吸了一口烟,打断我:“这栋楼,有些年头了。有些事,
看见了就当没看见,听见了就当没听见。”他顿了顿,浑浊的眼睛在烟雾后看着我,
“子时巡楼,签到就走,莫停留,更莫数台阶。记住老王的话。
”“老王他……”“他回老家了。”老张掐灭烟头,站起身,语气不容置疑,“准备巡楼。